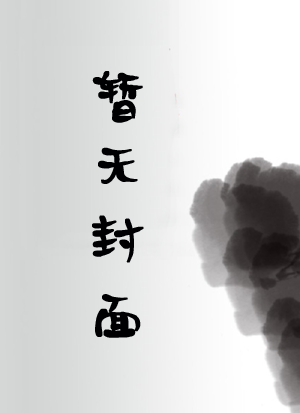年輕的皇帝很高興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議漸漸平息,雖然新黨和舊黨争議依然存在,但是舊黨和新黨中有一些傑出者都注意到,有些問題,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執行,是雙方都能接受的。
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進步得這麼快,就算有我這個推動者,也不可能。
曆史有其巨大慣性,這是個人的力量很難扭轉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這一點的人,都隻是一些身處中低階層的官員。
因為身居高位者,對争論陷入太深了,很難跳出來客觀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馬光這樣有大智慧且人格無礙的政治家,也無法抛棄政治上深深的成見,蓋因他們都是旋渦最深處的人。
我再一次很堅定的拒絕了皇帝給我的“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個位置說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現在不适合做宰相,我還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鋒。
我現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緊緊的依靠皇帝和下層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來赢得輿論的贊譽,用不斷獻策且免于朝廷紛争的方式來赢得皇帝的欣賞,用學院和學識來赢得下層士子的支持。
我的政治地位在這樣的策略下,必将不斷的鞏固。
皇帝很快批準了處于湖北境内的幾座鐵山給我,為了避嫌,我主動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員協助我。
這一次我動用各種力量,雇傭了三千多名優秀的鐵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
湖北的鐵礦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覺中,是沒什麼名氣的,我的想法還是在四川建立一個鋼鐵基地。
但是目前為止,我的打算隻能到此為止,一切等成功再說,畢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戰略縱深了。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開往湖北的鐵礦,我把這個地方命名為黑金。
然後我就把鐵匠中名氣比較大的幾個人叫來,向他們交待我的構想。
首先當然是要燒制耐火磚,然後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選爐址,再就是向他們解釋着我理解中的鐵爐,一個六人高的豎爐,用耐火磚砌成,橢圓型,十圍粗左右,煙囪高聳入雲。
旁邊爐子稍小,謂之平爐,中間用耐火磚砌成磚格以為蓄熱室,煙囪處用生鐵做了引風機,和豎爐平爐一樣,皆用水車鼓風。
平爐鑄槽邊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卻鐵水。
在爐邊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觀火。
我又細細說了煉鐵與煉鋼的一些事情,有人聽到生鐵可以直接煉成鋼,當時就有不信之色。
隻是懾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對。
就隻好按着我說的去思忖,有些鐵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經驗之談,我本來沒什麼實際經驗了,也就鼓勵他們去試。
因為是皇帝欽準的,我同時讓鐵匠建了五座高爐,慢慢總結經驗。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嘗試把泥碳燒成焦碳。
雖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磚的燒制,水車的制造都需要時間,當時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車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風了,不過這玩意倒沒我想的複雜,這些巧匠們很容易就做出來了。
第一個月的五個高爐,最後竟然塌掉了四座,還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燒出來的那都不能叫生鐵。
幾個鐵匠頓時有了懷疑,不過李一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還能堅持信念,他們還沒來得及見我,就被勸回去了。
于是那些有點名望的鐵匠就被聚到一起,開了個會,提出了許多細節上的修改意見。
我因為有做玻璃的經驗,倒是能夠很坦然的面對這些失敗。
隻要求他們盡力去試是了。
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與李一俠,他們的雄心壯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還用心用力。
我就每天喝酒,寫寫東西,籌劃着另一件大事。
相比起來,那個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還比我熱心些。
總算老天爺對我不薄,或者也是因為中國古代在煉鐵方面本身就有不錯的基礎,至少這個時代若論技術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在熙甯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爐生鐵出爐了,一爐就煉出了三、四噸。
然後在平爐用焦碳分開一煉,竟然就煉出鋼來了。
(鳴謝酒徒……技術細節來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歡呼聲震徹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俠,還有那個杜子建,都高興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聲高歌。
當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歡一夜。
其實以當時的曆史需要而言,中國所需要的鐵是有限的,在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為放礦工們的假,因為供遠遠過于求了。
另外中國富鐵礦較少,限制了中國在鐵器時代取得更大的進步。
但是我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我将創造一個鋼鐵與火器的時代,所以鐵器的批量生産,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因為鋼的成色不一,還有改良的餘地。
所以僅僅在休息一天之後,我就要求鐵匠們繼續努力。
做為了鼓勵,我下令給鐵匠們修建相當的舒适的房間,改善他們的夥食,并且增加他們的工資,并且許諾我将給他們的後代免費的教育。
這一切刺激着鐵匠們不斷的努力。
我又要求他們去設計車床和鋼管……這一次沒有鐵匠會懷疑我了,雖然這種工作的挑戰性真還不是一般的強,但是遲早有一天會設計出來吧。
不過現在還隻能靠鐵匠們用人工和簡易的工具打造各種鋼制工具。
到了熙甯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離開汴京半年之後,我終于又回到了京師,隻不過此時的我,還帶了一大堆鋼制的農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來并沒有太多的變化,唐棣、蘇鞏和石福盡心盡力的幫我打點一切内外事務,有一件事情讓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對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終于出現一家和我競争的印書坊,掌事的曾經在我的印書館做了一年半,是一個叫趙青芹的小夥子,據說他家裡也是個有錢的富商,對于這種商業間諜,我倒是很欣賞,至少他做為一個富家子弟能肯吃這個苦,就是讓人欣賞的。
趙記印書館開張以來,搶去了我們不少份額,石福更在和李三樸、趙樹福商議,怎麼樣擠垮對手呢。
隻是唐棣和蘇鞏對這種行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來再做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