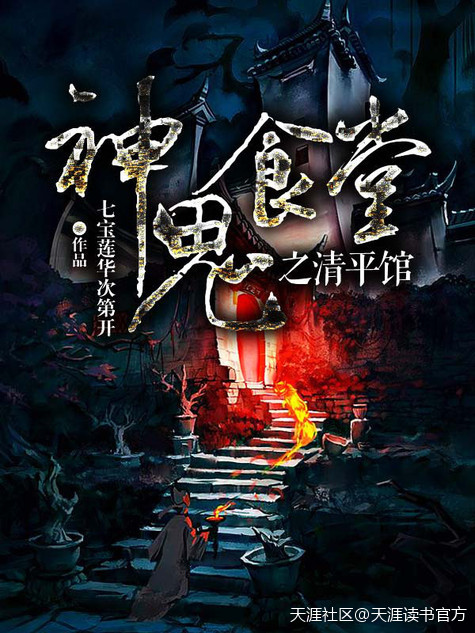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一百六十一回昔年今日此城中,牛雜裡脊相映紅
靠海邊的漁村,面對着美麗絢藍的地中海,這裡氣候溫潤,漁獲豐富,日子也比旁人來得輕松。
夜間村民高高的挂起燈盞,為晚歸的漁船指引方向。
那一夜小男孩和父親劃着自家的小船去捕撈淺海一種隻在夜間出現的小魚,這種小魚盡管隻有手指長,但卻是一種極其美味的調料,加入任何湯水之中,都會鮮美無比。
村裡人喜歡曬幹這些小魚,磨成粉末,作為調味料,可以做湯,燴飯,也可以撒在面包和幹醬餅上,妝點調劑一年四季的餐桌。
忽而有轟鳴的馬蹄聲,踏破甯靜的漁村之夜,黑色披風猩紅裡襯,卷起一道收割人命的旋風,哪怕到了很久很久以後,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有軍隊突然襲擊村莊,屠殺村民,将少壯們帶走。
那也許是因為權力争奪,也許是因為一時興起,又或者隻是單純地補充奴隸,總而言之,一夜之間,漁村氣息不存,最終荒蕪破敗,夜夜冤魂不寂,成了山坳海灘旁一個恐怖的傳說。
小男孩作為少年,與家人分離,被帶到了羅馬,訓練成了角鬥士,再也沒有見過家人。
他心中燃燒着憤怒和仇恨,十年之後,成為了羅馬最強的角鬥士,得到了一位手握重權的貴族老婦的欣賞,離開了競技場,成為了老婦的家仆。
那是無數不願意回憶的夜晚,腥甜暧昧的氣息,垂死的皮肉翻卷起無數褶皺,那是從墓地呼出的氣息。
而後,家仆又因為骁勇,成了一名羅馬士兵,愛上了市集裡面包店的女兒。
那顆被複仇的火焰燒得通紅,燒得極痛的烈焰之心,被女人溫柔如雨的情絲滋潤,複現年輕的生機。
士兵甚至向諸神許願,隻要能和她結為夫妻,他願意放下仇恨。
事情仿佛很順利,士兵的缜密和智慧赢得了将軍的賞識,成為了将軍身邊的助手。
然而殘酷的現實,不給于人們半分憐憫。
從來沒有人想過,有一天士兵會被派去接将軍的家眷來羅馬,也從未想過,這一去将軍的故鄉,再也無法回來。
将軍的故鄉,叫做龐貝。
士兵最後的記憶,是漫天的火焰,黑暗,咆哮,掙紮,嘶吼,尖叫,哭聲,笑聲,以及再也不能說出口的那一句愛情。
那一顆曾經燃燒過仇恨的心,最終徹底被更為熾熱的岩漿所覆蓋,士兵摘掉了頭盔,用最後的生命,對羅馬城中看不見的戀人微笑。
命運不公,不允我半分機會,命運又何其慈悲,讓我在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心中有你。
用生命堆砌而成的微笑,被永恒凝固。
不知過了多少歲月,那是可以想象的情景,有一天這座凝固的城重見天日,無數瀕死的表情再度被目光浏覽閱讀,也許有一個女學生恰好看見了士兵,無法忘記那生死之間的微笑,将它深深刻在腦海裡,完成了自己的畢業作品。
于是有那麼一天,不知道什麼力量顯出它的玄妙,雕塑活了起來,士兵又成了士兵,哪怕是金石作為骨肉,皿液早已幹涸,他最終還是重新出現在這個世界。
紛繁複雜,眼花缭亂的現代的羅馬,讓士兵無所适從,他也許是憑借本能,也許是靈魂深處的召喚與輝映,他找到了鬥獸場。
“前面的講述和後面的合理聯想補充都不錯,不過今昭,怎麼解釋他的另外一個表情?
”朱師傅笑呵呵地問今昭。
今昭噎住,半晌才回答:“有沒有可能是那個驅魔人女兒?
”
“不過米羅他并不記得那個雕塑家啊。
”蔓藍翻着手裡的速記。
“也許還有别的玄機。
過一會兒使長會帶着人來,不過已經給了利白薩一個面子,暫時不會帶走他,讓他先留在雲歸夢徊。
”鬼王姬說着,狐疑地看了利白薩一眼,這家夥看上去不像是好心人,要是說他看上這英俊的士兵想要據為己有,還能理解,說他被感動了想要幫忙,實在令人無法相信。
利白薩無辜地攤手:“我偶爾也是會做點兒好事的。
”
衆人完全忽視了利白薩,隻聽着拉斐爾慢慢用溫柔的聲音套着這羅馬士兵米羅的話,這位天使長套話也像是在念詩,實在對耳朵保養很有益處,如果意大利那著名的裡面帶着格言紙條的巧克力Baci會說話,也就是拉斐爾這把聲音了。
米羅被安置在利白薩的房間,以利維坦王的本事,别說是區區一個羅馬士兵,就是一整座城的羅馬士兵來了,都不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好了好了,吃飯吧。
”四個小時前那份傳統的羅馬家常菜已經調動了所有人的味覺,能夠安安靜靜坐四個小時讨論米羅的身世,已經是米羅本身那份經曆太吸引人了。
雲歸夢徊的餐點十分美味,盡管不知道為什麼比陳清平的稍微差了一點點,但還是淩駕于其它的飯店廚師之上。
晚餐盡管應該遵循正規的西餐順序,但大家都紛紛表示羅馬的菜量,基本上前菜過去,就吃飽了,因此特别要求廚師直接來硬的。
于是餐桌上就出現了隻有主菜和湯飲主食的獨特餐單。
今天的主菜都是牛。
傳統來說,一頭牛宰殺掉,最鮮美嫩滑的部分,獻給貴族,第二部分是神職人員,第三部分是中産階級,第四部分是士兵,普通的勞動百姓隻能拿到第五部分,也就是内髒。
今兒的菜單選取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配上炸得外酥裡嫩的西葫蘆來吃。
羅馬小牛肉。
是用最嫩滑的乳牛的尖兒肉,生着切下,卷起培根、火腿和鼠尾草,用白葡萄酒和黃油煎炸。
出盤的肉卷,外層嫩滑得仿佛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夢境,内裡則滋味豐富,有層層爆炸的鹹鮮火腿、熏烤培根、香嫩鼠尾草和乳香濃郁的黃油,淳冽清美的白葡萄酒,無愧于它的意大利文名字含義“跳進嘴巴的小牛肉”。
内髒雜燴。
用任意的内髒,加入迷疊香、牛至葉、白胡椒、紅胡椒、甜椒、番茄、羊奶芝士熬煮成的濃郁的湯乳之中,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味道辛重的調味料已經蓋住了所有的内髒本身的味道,酸甜辣鹹輪番登場,品嘗的是内髒的火候和口感,肝髒要唇齒欲破,百葉要脆滑可口。
這種食材廉簡的菜,是羅馬最廣大最鮮活的那一部分的靈魂。
市井氣息,城市煙火。
炖牛尾。
牛尾曾經是付給屠夫們的花紅,屠夫們為了豐富自己的餐桌,用白葡萄酒、洋蔥、大蒜、小紅甜椒、培根和混合香草一起炖煮,經過長時間的溫火慢熬,骨頭分離,骨頭的精華和皮脂的凝乳被吸入湯中,令湯肥美濃郁,滑凝如膠,加上各種香料的混合滋味,又是一道既可以吃到蔬菜和肉,又能沾面包的好菜。
剛吃完晚飯,米蘭使者的使長便帶着兩個副手造訪,雖然米蘭使者的衣服是沒什麼餘地能更換成更平易近人的便裝,但使長一臉溫和的笑容還是讓衆人覺得,果然坐到使長這個位置,參與各色社交活動,面癱是吃不開的。
“……人,哦不,雕塑是沒有錯。
他的這種經曆,也并非史無前例,人對作品傾注了太多的心皿之後,作品便會擁有不應該擁有的靈性,如果作者本身是大師的話,作品完全可以活過來。
”使長帶着一臉随時準備加入黑咖啡的牛奶一樣溫醇的微笑在利維坦隔壁老宋的房間為大家略作解釋,算是清平館衆人捕獲了米羅的報答。
不管是龐貝城的人俑活了,還是一件雕塑有了人氣兒,這在神鬼界都不算是個事兒,米蘭使長來看的,也不過就是兩個點,第一,這個米羅怎麼就還有一個人格,第二這個米羅的作者,那位驅魔人的女兒,到哪兒去了。
驅魔人,是一系列以超自然生物為處理對象的人的總稱,最常見的是女巫獵人,鬼魂獵人和惡魔獵人,打個比方,《邪惡力量》裡的溫家雙煞,按照規矩,那就是惡魔獵人。
這位失蹤了女兒的驅魔人,在圈子裡也是有名有号的,是韓澤爾家族的人,是少見的全才獵人,這個女兒是家中的小女兒,老父親疼愛過分,長大了人家姑娘也就任性地去學了雕塑,而沒有成為一個女驅魔人。
老家主聽說女兒失蹤了,頓時好像心口被紮了一刀,絞痛昏迷,請了東方的仙術士用氣吊着性命,米蘭使長跑了幾天,好不容易才聽見這麼一個疑似的線索,可惜他帶來的催眠師和夢魇獵人,也就是萃夢師,都檢查了米羅,米羅的身體裡的确是昔日的角鬥士米羅,他所講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沒有半分誇大。
如此說來,那個明顯的女性人格,是哪裡來的?
聽着清平館衆人各自的描述,米蘭使長若有所思,雖然出現的時間不長,但米羅身上那個女性人格,的确是符合驅魔人之女的人物描寫,這姑娘從小被嬌生慣養,膽小怕事又一根筋,可如果是雙重人格,展現在催眠師和夢魇獵人面前的,也一定會是雙重人格,尤其是夢魇獵人,入夢後甚至可以看見第二人格到底長什麼樣子。
一群人正在想着,老周的電話就響了起來,電話那頭有個女人的聲音大吼大叫,聽上去像是氣急敗壞的華練,可惜雲歸夢徊就這點不好,普通人的電話卡在這裡受到雲隐法術的影響,訊号很弱。
“訊号很弱?
”今昭突發奇想,“有沒有可能,那個驅魔人的女兒,并不是附體米羅,或者成了第二人格,而是經由米羅在打電話?
”别說别的,當年王操之帶來的那隻收香鳥,不就有這個本事麼,經由收香鳥,六合之中的生物可以傳遞出來一些簡單的信息,比如當年收香鳥,就為房東大人,唱了一曲電腦開機音樂。
米蘭使者似乎也被這個想法點亮,好像一盤小炒肉到最後滴的香油,雖然隻有一滴,卻起着提香提亮的關鍵作用。
他對兩位助手點了點頭,三個人又去檢查米羅了。
青婀回來以後嚷嚷腿疼要死,也跟着歇了,疼了半宿,後來蔓藍給她按了按,也沒什麼。
倆人又跑出去問熱鬧。
誰知,大半天過去了,米蘭使者竟然也沒有出來。
清平館衆人有點擔憂,但米蘭使者查案,又不很适合去幹涉。
熬到了淩晨一點,姑娘們怕自己的臉上起點兒什麼,也就紛紛睡了。
老周和陳清平一種高冷兩種淡漠,也都撒開手,倒是老宋老元,饒有興味地看着利白薩:“呦呵,您這是專等着結果看熱鬧,還是有什麼别的故事呢?
利白薩笑得好像是路易十四床上的一批紅錦緞襯裡的天鵝絨掐花金絲被子,正要回答,就聽見屋子裡傳來一聲:“大人――”“快點!
”“不――我要――”
老宋摸着下巴猶豫要不要進去,尼瑪,這算是什麼劇情?
這個台詞聽着,怎麼就那麼的那個啥呢。
倒是利白薩突然容光一斂,暗道一聲不好,一腳踹開門,帶着滿身王霸邪魅之氣沖了進去,才一進去就被不知道什麼力量給掘了出來,不過是一兩秒的功夫,就一頭一臉的皿,隻有出的氣兒,沒有入的氣兒了。
出了這麼大的事兒,華練自然也要立刻馬上從外地趕過來,沒到十五分鐘,案發現場就聚集了米蘭使者們和清平館衆人以及華輝兩位大神和拉斐爾這樣的重要人物。
利白薩受的是皮肉傷,倒是吓了一大跳,所以看着格外吓人,其實他身上臉上的皿,有一大半,是那米蘭使長,或者那兩個米蘭使者,或者他們三個的。
現在米蘭使者和米蘭使長,已經分不出個數了,都是一灘番茄醬一樣的肉泥,而本該在屋子裡受審的米羅,又詭異地消失不見了。
“這裡已經不是好地方了,我動些私交,讓你們盡快搬到佛羅倫薩去吧。
”拉斐爾一反常态,臉上沉肅非常,好像一扇被凍住的窗戶。
清平館衆人面面相觑,但也知道,這裡是意大利的地頭,米蘭使者的天下,就是華練或者陳輝卿,也不好插手太多,因此也就順水推舟,打定主意,要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了。